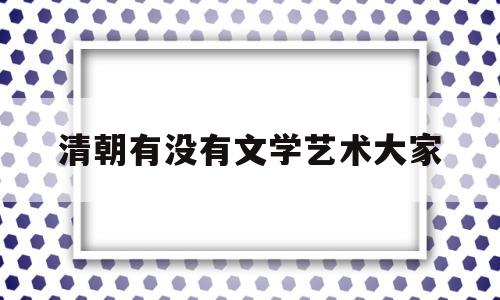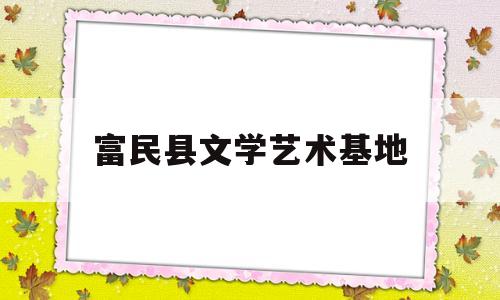人物小记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
小说家。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中华民国上海公共租界。本名张煐,后因入学需要,母亲黄逸梵(又名黄素琼)以英文名Eileen译音,易名爱玲。
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长女,父亲张志沂为清朝末年著名大臣张佩纶的儿子,母亲黄逸梵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之孙女,即前桂平梧郁道黄宗炎的女儿,继母孙用蕃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因此,张爱玲出生名门,受到了极好的教育,特别是当代处于中西合璧价值观的形成。上海沦陷时期,陆续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等中、短篇小说,震动上海文坛。1952年张爱玲以完成未完成的学业为名离开中国大陆,其后赴美。在美国期间翻译了清代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韩邦庆所著),又写了文学评论《红楼梦魇》。张爱玲一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漂泊于上海、香港、天津、美国各地,最后在美国定居,并于1960年取得美国国籍。早在之前,1956年时,张爱玲就已经和大自己36岁的德裔美国人赖雅结婚,赖雅逝世后,张爱玲在美国终老,1995年9月8日,因为动脉硬化心血管病去世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市西木区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享年74岁。
张爱玲一生游走中国各地,自谓“我的上海话本来是半途出家,不是从小会的。我的母语,是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
我们在篇首举出一般创作的缺陷,张女士究竟填补了多少呢?一大部分,也是一小部分。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在她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优点对作品真有贡献的,却只《金锁记》一部。我们固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
《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题材而论似乎前者更难处理,而成功的却是那更难处理的。在此见出作者的天分和功力。并且她的态度,也显见对前者更严肃,作品留在工场里的时期也更长久。《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还有那漂亮的对话,似乎把作者首先迷住了;过度的注意局部,妨害了全体的完成。只要作者不去生活在人物身上,不跟着人物走,就免不了肤浅之病。
小说家最大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生活经验是无穷的。作家的生活经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富,决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
巴尔扎克不是在第一部小说成功的时候,就把人生了解得那么深,那么广的。他也不是对贵族,平民,劳工,富商,律师,诗人,画家,荡妇,老处女,军人……那些种类万千的心理,分门别类的一下子都研究明白,了如指掌之后,然后动笔写作的。现实世界所有的不过是片段的材料,片断的暗示;经小说家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心,宗教家的热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身为故事中的角色(还要走多少回头路,白花多少心力),陪着他们身心的探险,陪他们笑,陪他们哭,才能获得作者实际未曾的经历。一切的大艺术家就是这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这些平凡的老话,张女士当然知道。不过作家所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的声音。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上。任何细胞过度的膨胀,都会变成癌。其实,彻底地说,技巧也没有止境。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人生形象之多,岂有一二套衣装就够穿戴之理?把握住了这一点,技巧永久不会成癌,也就无所谓危险了。
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何况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金锁记》的作者没有理由往后退。
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它只能使心灵从洒脱而空虚而枯涸,使作者离开艺术,离开人,埋葬在沙龙里。
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或者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我不是鼓励悲观。但心灵的窗子不会嫌开得太多,因为可以免除单调与闭塞。
总而言之,才华最爱出卖人!像张女士般有多面的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作家(绘画,音乐,历史的运用,使她的文体特别富丽动人),单从《金锁记》到《封锁》,不过如一杯沏过几次开水的龙井,味道淡了些。即使如此,也嫌太奢侈,太浪费了。但若取悦大众(或只是取悦自己来满足技巧欲,——因为作者可能谦抑说:我不过写着玩儿的。)到写日报连载小说(Feuilleton)和所谓Fiction的地步那样的倒车开下去,老实说,有些不堪设想。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彩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只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我知道作者发表的决非她的处女作,但有些大作家早年废弃的习作,有三四十部小说从未问世的记录。)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文章来源:《傅雷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版权声明:本公众号编辑和转载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文章仅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学院立场。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处理。